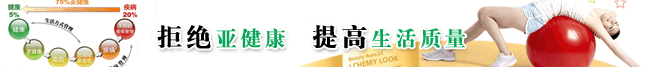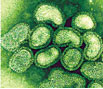我是1996年12月份第一次知道艾滋病的。当时,参加北师大红十字会宣传艾滋病的活动,但不知道艾滋病意味着什么。
1997年,我加入了北师大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当了外联部长。有一天,我买了一张盘《费城故事》,这部电影扭转了美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我看完很感动。
当时,我也想做成中国的“费城故事”,找到一个感染者,敢于站出来,我们配合他,树立一个形象,想带动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减少歧视。卫生局说,不可能,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1998年,我认识了一名第一位公开身份的感染者,叫宋鹏飞。每周3天去宋鹏飞家里,陪他聊天、下棋、教他电脑,而且在媒体作宣传,消除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他父亲说,宋鹏飞公开身份后,邻居往他家里扔石头,让他们搬走,要不走就拆了。
到了2000年,我准备读研,继续读天文。《健康人》杂志的记者问我,你为什么不愿毕业后去做艾滋病民间组织。我当时跟他说,我看不到做艾滋病能做出什么来,它的意义在哪儿?我们帮宋鹏飞一年多,完全没有改变,仍然只有宋鹏飞一个人站出来,没有人再敢于站出来,弄得我们没有信心,甚至怀疑国内到底有没有30万感染者,我们不想把10年甚至更长的生命花在一个人身上。
后来,看媒体报道知道河南一个村输血感染了艾滋病。我和河南一家媒体的记者喻尘联系,喻尘告诉我说:“现在你去文楼村,会被警察原路遣返。”我们就到开封的尉氏县和商丘的睢县,去一些家庭,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死亡的故事。11个大人,他们都是艾滋病,至少有两个孩子,过几年他们都会去世,那他们的孩子该怎么办?
在河南的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跟别人讲,我去了河南,如果是平时到哪个地方旅游,交了朋友,过了几年去还跟他们聊天,跟他们玩;但这个地方的人,如果再过半年去,就只能去扫墓,这些人都可能去世。那种感觉,就好像身边有个花瓶要摔下来了,你明明知道它还要摔下来,但你没法接住它。忘了是在梦里,还是真的就哭了。看了他们之后,就决定要做艾滋病这个事情。
我们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叫夏青。2001年夏青只有8岁,我们去他们的村子后留下了电话。三个月后,夏青的父亲跟我们联系,来到北京。那个时候,治疗艾滋病只有国外的药,很贵,国内没有免费药,治病需要很多钱。我们劝说夏青公开身份。
《北京法制报》报道了夏青,后来湖南电视台也给夏青做了一期节目。2002年2月份,《翠花,上酸菜》剧组募捐到6万元给夏青。夏青正常吃药治疗,回到了开封,政府给夏青解决了入学问题,现在大概上小学四年级。
救了一个人的命,心里很有成就感。我心里还想找到一个感染者能站出来,告诉别人感染者和正常人一样,并不可怕,这样会降低对感染者的歧视。但是,这样的人很难找。
2002年,我自己跑到艾滋病村,当地村民接应我,将感染者的口述拍摄下来,第一个影像资料出来了,刻成了VCD发给卫生部和一些媒体看。
在河南,大人死亡时说:“你们想想办法,别让我们的孩子成孤儿。”帮不了大人,帮小孩,我想需要一个组织来做。2003年,注册了东珍艾滋病孤儿项目,帮助艾滋病孤儿。可是,后来发现在资助的孤儿中,有造假的。村里的“能人”把资助的名额,给自己的家人或者亲朋。
后来,我们说,资助不是一个长久的好办法,更多的是给他们教育和心理辅导,我们想办一个孤儿院,接他们到商丘市上学。学校成立后,收了20多名艾滋病孤儿。一直到2003年12月份,当地政府投资170万建成阳光家园,将这些孩子全部接收。
现在回想,那个时候主要做成了三个事情:一个是东珍孤儿学校的20多名孤儿有了地方接收;二是因为办艾滋孤儿学校,更多的媒体关注到商丘和河南艾滋病村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吸引了更多机构和个人关注河南的艾滋病问题。
现在艾滋病救治方面,民间组织的作用比以前是小了,能力方面有所欠缺,主体上是政府方面在做,主体的资助来自政府,包括国际上的一些捐助。其实,不在乎民间组织强还是政府强,关键是要做正确的事情,现在大家都还差一点。
来源: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