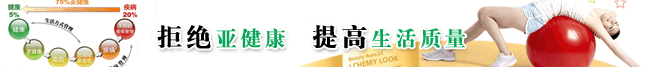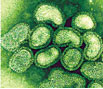每出现一种新型疾病,国内总会有一些医生趁机吹嘘其医术、药厂趁机推销其产品,再新奇的疾病,也斗不过其祖传药方。这一次的新型流感也不例外,甚至各省、各市都推出自己的药方,似乎流感病毒也会入乡随俗。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药方有效:医生的宣称、患者的证词和官员的认可都不是证据。现代医学对药物采取的是“无效推定”,没有证据证明有效,就不承认其有效。这些祖传药方也就只能在国内自得其乐。如果一种药物被证明了有效,那就不会只限于一国一地,全世界都会使用。所以虽然国内有无数的祖传药方声称对新型流感有疗效,国内医院治疗时首选的药物仍然是达菲,因为它的抗流感病毒的疗效已被世界公认。
达菲的研发始于1992年年底。当时,美国加州一家生物技术小公司“吉里德科学”根据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的分子结构,设计出能够抑制其活性的化学分子,加以人工合成,然后检验是否真能抑制流感病毒的增殖。在测试了600多种化学分子后,1995年年底,一种后来称为达菲的新化学物质被选中了。
体外的实验证实达菲能够强烈地抑制流感病毒。但是离体实验未必能反映人体的情形。药物有可能无法被人体吸收,即使能被吸收也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还可能对人体产生不良反应。这些是无法在离体实验中观察到的。
出于人道的考虑,不能直接拿人来做试验,先要在动物身上做。因为不同种类的动物对药物的反应可能会不同,往往要用到两种以上的动物。研究人员分别用小鼠、大鼠和狨猴做毒性试验,又在感染了流感病毒的小鼠和雪貂身上做治疗试验,发现达菲很有效,而且没有明显的毒性。
但是动物和人的生理毕竟还是有所区别,对动物有效、毒副作用小的药物,对人体不一定如此。只有临床试验才能最终决定一种药物是否对人体有效和有何毒副作用。然而,临床试验的费用非常高,往往需要上亿美元的资金,不是小公司负担得起的。“吉里德科学”在大制药公司中寻找合作伙伴,最终和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瑞士罗氏达成协议。
1997年3月11日,第一位试验对象吃下了从没有人吃过的达菲。试验的第一阶段目的主要是观察药物是否会出现急性毒副作用,以及人体对药物的吸收、代谢和排泄情况,在几十名健康人身上试验就可以了。在发现达菲能被人体很好地吸收,而且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之后,就进入了临床试验的第二阶段。
在第二阶段,要在上百名病人身上做试验,看看药物是否有疗效,用多大的剂量会有效。但是此时是5月份,不是流感季节,找不到流感病人。研究人员不想坐等流感季节的来临。他们找来117名健康志愿者,往他们的鼻腔里塞进一团浸泡了流感病毒的棉花,让他们感染上流感。
第二阶段通过后,开始了最关键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要在上千名病人身上做试验,而且必须是实际生活中的流感病人。但是靠症状很难把流感和普通感冒区分开,误诊率高达70%。要确诊就必须检测病人身上是否有流感病毒,但是等检测结果出来,病人病情已自然缓解甚至痊愈了。不过,在暴发流感的社区,一个有感冒症状的病人患流感的可能性高达70%,可以用他们来做试验。
罗氏公司联系了世界各地300多名医生参与试验,等待1997~1998年冬季流感的来临。达菲只在流感症状出现的36小时内使用最有效,但人们一般不会在得了流感后马上就去看医生,所以虽然有这么多医生帮忙,要找到合适的试验对象仍然不容易:1997年11月底找到第一位,一直到1998年4月15日才找到第1355位也是最后一位试验对象,少于预期的数量,也只能将就了。
但是怎么知道达菲对这些病人确实有疗效呢?一个病人吃了达菲之后,病好了,并不能就证明达菲确实有效。流感(以及许许多多疾病)不吃药也会自然好转、痊愈,在接受了“吃药”的心理暗示后,即使吃的是无药效的假药(所谓安慰剂),也会好得更快。为了排除这种情况,要把病人分成两组进行比较,一组吃达菲,一组吃外观相同的安慰剂。怎么分组很有讲究。如果由研究人员来挑选病人,就可能有意无意地把病情较轻的病人挑选入新药组,使得新药组的疗效过于显著。因此病人将进入哪一组完全由随机产生的编号来决定,而不是人为地挑选,以保证两组的病人有相似的情况。
为了排除心理暗示的影响,不能让病人知道他分在哪一组。而且,医生、研究人员也不能知道病人的分组情况(所谓双盲)。如果他们知道了,可能会对新药组病人更精心护理或施加暗示影响病人,在判定疗效时,会倾向于更正面评价新药组病人,更负面评价对照组病人,只收集对新药有利的数据而忽视不利的数据等等,从而出现主观偏差。分组情况由第三方掌握,最后才解密。
1998年7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试验结果都收集到了,很快就统计出了结果:服用达菲的病人与服用安慰剂的病人相比,病程平均缩短1.3天。1999年3月,罗氏公司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提交达菲上市申请,10月,被批准上市,流感季节刚好来临。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