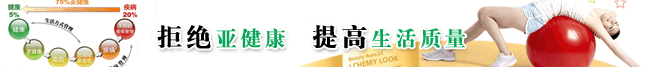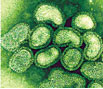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坚持不懈地在世界体坛进行反对服用兴奋剂的斗争。作为奥林匹克运动道德观的坚定护卫者,国际奥委会不仅在四年一次的奥运会上,而且在世界各种体育比赛中都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
国际奥委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协调任务,出资召开反兴奋剂会议,鉴定并批准合格的兴奋剂检测实验室,公布权威性的禁用物质与方法名单,而且最重要的是,对已经陷入道德危机的体育运动进行道义上的正确领导。
运动员服用药物并非什么创举或新闻,其实早在1896年现代奥运会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中叶,就曾有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报道。18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次运河游泳比赛中,也发生了参赛选手服用兴奋剂事件。1879年,又有关于自行车运动员在自行车六日赛中服用兴奋剂的报道。在1908年奥运会上,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多兰多·彼得里跑到终点处虚脱倒地,被认为是服用了士的宁(strychnine)。从那以后,小剂量服用士的宁就常被用作一种兴奋剂。为了夺取比赛的胜利,运动员们互相效仿,滥用药物之风愈演愈烈。
1960年,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纳德·延森在进行公路自行车比赛时突然死亡。几乎可以肯定,他是因为服用兴奋剂而衰竭致死。翌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成立于希腊雅典,由阿瑟·波里特爵士出任主席。
1964年东京奥运会,对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了小规模的某些药物检测,这也是首次在奥运会上进行药物检测。三年之后,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重组。之后,在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实施了全面的药物检测。
实行药物检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同日益增多的滥用兴奋剂现象做斗争。由于合理安排、程序规范的兴奋剂检测可以轻而易举地检查出运动员是否服用了这类药物,自70年代初服用安非他明等药物的运动员就已明显减少。国际奥委会,特别是其医学委员会下属的兴奋剂分会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其实是激素类药物的使用。这类药物早在60年代初就已被运动员广泛使用。
在70年代,人们还预见不到合成代谢类固醇会有那么广阔的应用范围。最初,仅认为只有田径运动的一些投掷项目、举重以及搏斗项目中的那些重量级运动员,才有可能靠增大肌肉块头获益。然而,其它项目的运动员后来发现,合成代谢类固醇能使他们在大运动量训练后更快地得到恢复,而且许多项目的运动员——从长跑到游泳,从短跑到自行车——都可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