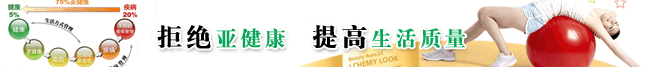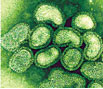昨日召开的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会议给三类精神障碍者带来好消息,《武汉市精神卫生条例(草案)》拟明确规定,对家庭贫寒、生活无着的“三无”精神障碍者实施来自政府的医疗救助。这三类患者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抚)养人的精神障碍者;生活贫困的重性精神障碍者;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者。
刚看到这则新闻时,笔者和许多公众一样,为武汉政府推出这项旨在援助贫困的精神患者及其家庭、预防和减少公共安全隐患的善政而感到欣慰不已。可是,转念一想,这些患了特殊疾病的患者得到了救助,可是那些患了其他疾病又没有处于医保覆盖的“三无人员”又当如何呢?难道只是因为他们所患的疾病没有对他人及社会的潜在危险性,公权部门就可以等闲视之让他们自求多福吗?
在现有医疗体制下,“三无人员”基本是无缘被医疗保障体系所覆盖的。即便是那些处于医保覆盖下的企、事业职工,新农村合作医疗的参保者也经常会被医保赔付率过低、过窄的保障病种、太过严格药品、器械使用限制而倍感无奈。现行的医保体制为何如此弊端百出?以至于让广大的普通公众多年来都深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所困扰?
据卫生部主管的《健康报》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在我国卫生总费中,政府的投入仅占17%左右,企业、社会单位负担约占27%,其余56%则由个人支付。相较之下,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卫生总费用,美国政府负担45.6%卫生总费用。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负担的卫生费用比例也远高于我国。值得一提的是,这17%的政府投入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体系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公务员、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有正式编制的职工。在此范围之外的绝大多数的普通公众只能自己花钱支付医疗费用。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则对公立医院获得的财政投入在医院的运行成本中的比例自然是逐年下降。很多公立医院甚至成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在这种状况下,公立医院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维持正常的运转自然难以抑制逐利的冲动。尽管卫生主管部门曾顺从民意多次的推出限制药品最高价格、降低医疗检查费用等措施,希冀减轻公众的医疗负担。但是总是收不到效果。因为医院财政是部分或全部的自主收支,所以卫生主管部门控制不了医院的财政也就管不了医院的具体的运营活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医院总是能很快找到应对这些“限价令”的办法。院方或者是定指标让医生搞创收性医疗,或是停用没有多少利润的药物,或者诱导病人接受价格较高的医疗项目。如此一来,我国公众的总医疗费用自然是降不下来的。
获得社会上一些慈善组织和个人的力量的援助曾一度是那些患病穷人所寄予厚望的获得医疗救助的方式。但是,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民间慈善组织的数量和力量都还相当的有限。其管理和运作的体制也还有待成熟。很多慈善组织寻在救助对象的渠道只限于各种媒体的报道。但是媒体做的不是慈善事业,他们首先要考虑是公众对新闻是否感兴趣。而普通公众不是总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去关注这些亟待救助的病人。从这些现实的情况看,慈善事业短期内难以成为解决救助社会救助的主要途径。让国内每一个公众都病有所医这份沉重的社会责任绝不是公众们靠社会救助或者自力更生就能担负得起来的。
由此可见,完善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才是让每个公民都能病有所医的根本途径。让每一个公民都能病有所医绝不能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也不能只是难以企及的遥远理想,它更应该成为政府义不容辞要担负起来的责任和义务。
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