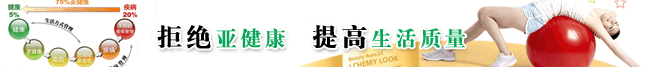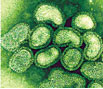2007年6月,关宝英从北京市卫生局疾控处处长任上退休。
与大多数安享天年的“老干部”不同,55岁的她选择了更富挑战性的职业——领导一家非政府组织(NGO),继续艾滋病的防治。
从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与这种敏感的绝症打了23年交道。
其间,这位被HIV感染者称为“关妈”的女性,直面多次挑战与选择。
年过花甲的关宝英身材高挑,衣着考究。一头大波浪卷的披肩发和淡淡的口红,在同龄人中并不多见。
“我很在意自己的形象。早晨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用发卷做头发,然后才开始洗漱。”她说,“这样,不仅能给别人一个好印象,也会让自己感到更自信。”
家境的富足让关宝英在生活中没有太多烦恼。虽然青春不再,但她还是和年轻人一样,喜欢逛街,定期美容。约人谈事时,也爱把地点选在咖啡厅,要上一壶价格不菲的普洱茶。
但当谈到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现状时,这位平日里一脸笑容的退休官员,便忧虑加自责地说,“我们失去了最佳的控制时机”。
从1985年参与处理国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开始,关宝英已经和这种绝症打了23年交道。HIV感染者们亲切地称她为“关妈”;西方媒体称,“中国阻止艾滋病,需要来自关宝英这类人士的努力”。
第一次接触患者: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
1975年,在结束7年插队生活后,23岁的关宝英回到北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医学院学习。
但毕业时,她被分配到北京市卫生防疫站,从事疾病预防工作。一年半后,又借调到市卫生局负责筹备组建防疫处,直到正式调入。
这一去就是26年,直至退休。
这让她有机会接触艾滋病。1987年,北京市成立了首个性病防治专业机构——皮肤病防治研究中心,关宝英负责分管性病艾滋病工作。不久,她接触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触动太大了!那是1990年,佑安医院收治了一名援非(洲)的医务人员,被确诊为艾滋病。我去病房看过一次,就跟国外宣传画上的一样,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仿佛一个大骷髅。”
尽管作为医务人员,关宝英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她仍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回家后,把全身上下的衣服脱在门外清洗后,才进家门。这在当时并不奇怪。佑安医院在这名患者死后,将他病房内的所有物件全部焚毁,床、板凳、桌子、被褥??连他交费时给的美元,也放在微波炉里烤了又烤。
1995年的一次考察,让关宝英对艾滋病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考察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最早发现艾滋病的美国。
“在那儿,艾滋病患者并不像国内隔离治疗,而是与其他普通病人混住在一起。一些社会工作者还自发地帮助感染者争取合法的权益,比如救济、医治、工作等。”
在半个月的考察过程中,给关宝英印象最深的是一幅挂在一个艾滋病患者床头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患者与一名好莱坞当红影星相拥而笑。看完,关宝英觉得很惭愧。
回国后,关宝英改变以往站得老远和感染者交谈的工作方式,试着与对方握手。第一次握手,没想到对方的反应比她还强烈。
也正是这个简单的举动,让关宝英开始走近他们。之前,她去病房了解情况,他们甚至不愿让她看见自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