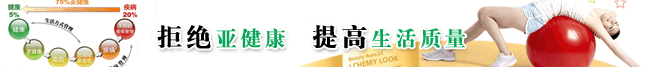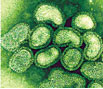大剂量化疗的效果很理想。到6月中旬,常规检查已经无法发现体内的癌细胞,“全家人都感到欣慰”。到此时,治疗费用又增加了8万,这不包括一家四口在北京学知桥边每月两千元的租房费用。
苗浴光的姐姐大苗在北京联合大学教书,她和父亲一样,献出了自己的造血干细胞。通过配型,父女二人都可以帮助小苗进行骨髓移植。
在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一次的腰椎穿刺。
6月25日,一种名为甲胺蝶呤的药物被注射进苗浴光的腰椎。
由于上海医药集团华联制药厂生产环节质量控制不严,将另一种只能用于静脉注射的药物——硫酸长春新碱——混进了甲胺蝶呤。腰穿之后第3天,苗浴光在走路时突然摔倒,自此以后,她的腿脚开始麻木,摔跤成为家常便饭。半年之后,当记者在苗家的出租房里见到苗浴光时,她的下肢已经彻底瘫痪。
小苗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年过五旬的父母除了暗自垂泪,在已经瘫痪的小女儿面前不敢流露出一丝绝望的情绪。
3月2日下午,老苗重新核账:到目前为止,仅仅苗浴光的医药费已经达到了40万,全部是自费。
苗浴光的花费,并不是白血病患者中的顶级。来自汕头的对外经贸大学2004级本科生熊云(化名),在受到“硫酸长春新碱”伤害之前就已经花费了50万元之巨,“好在学校报销了其中的30万”,熊云的母亲说。同时,在受到假药伤害之前,她已经成功地做完了骨髓移植手术。
东北人老苗觉得小女儿“点儿背”,和熊云相比,自己小女儿的旧患未除,又添新病;另外,“如果她早半年,辽师大会管她;晚半年,大连海关也会管她;都是公费医疗”。
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三大医保体系之上和之下,分别是公费医疗与自费人群。苗浴光不幸就在后者中。她在2007年的两次“点儿背”,让她从天堂跌入了地狱。
公费也有级别
和已经当上大学老师的姐姐大苗一样,苗浴光从小就是一个好学的孩子,一直努力向上。19岁那年她考上大学,在不经意间结束了自己没有医保的历史。
2006年初,小苗一边找工作一边报考公务员,因为分心而没考上。次年,她全力以赴,终于在上千人的竞争中胜出,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连海关的大门。
“如果她的第二只脚也能踏进去,也不得这场病,我苗家就是生活最好最幸福的家庭。”老苗说。
仅从医保这个角度而言,成为公务员和成为大学生都是公费医疗,但后者属于事业单位。社保资深学者、武汉大学教授王保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务员看病由财政兜底,即上不封顶,花多少都可以按级别报销绝大部分。而事业单位虽然名义上也是没有封顶线,但因资金来自上面拨的人头费,往往不够,如果单位‘创收’不足,医疗费报销就大打折扣。”
由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对外经贸大学生熊云治病只能报销50万当中的30万,而一位权威经济学家却花费了中央政府千余万元。
“同时,公费医疗的费用长期以来没有公开,民众并不晓得,公务员们究竟看病花了多少钱。”王保真说。
对公费医疗的开销数字,《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卫生系统和劳动保障系统多方求证,均被婉拒。只有一位中央部委的相关负责人说了一个大概的数字:在我这里,每天一台宝马车。
换言之,仅仅这一个部委,一年就要花上亿元的医疗费用。
目前唯一在公开场合对这一数字有所披露的,是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2006年9月,殷大奎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健康产业论坛上“放炮”称,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当时,全国卫生总费用约为7000亿元/年,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17%,约1190亿元,这里面的80%——也就是952亿元,用在了850万党政干部身上,其他13亿人分享其余的20%——区区的238亿。
“福利是刚性的,很难削减。”王保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