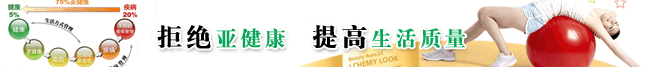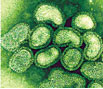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当时合作医疗是队办队管,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在大队的合作医疗站付5分钱(还有的地方不付)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费用从集体公益金里出。”不过那时农民要求不高,小毛小病几粒西药或者一把草药就行了,大队一年的开销也不过几百元。而且合作医疗只限于村里(大队),如果到乡卫生院或者区里、市里的大医院,医药费还是要农民自己掏钱。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地区由于村办集体企业比较发达,合作医疗还能维持。上世纪90年代才是“最最困难”时期,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倒闭,合作医疗只能算苦苦支撑,规模萎缩。虽然已经发展为队办乡管,即在全乡的范围内进行统筹,但医疗费用也在不断攀升,而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大概在15%左右。
陆国荣回忆,当时农民参保率仅40%-50%。“后来我做了镇卫生院的院长。镇卫生院也举步维艰,一方面农民看不起病、病人少,一方面没有集体经济的依托,生存都成了问题,提高为农民医疗服务的水平也成了一句空话。我当时意识到,农村合作医疗要维持、发展,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实行制度化的组织和财政支持,单单靠农民自发合作、集体低水平的扶持,撑不下去了。而没有合作医疗这个底,农村基本医疗体系也就完了。”
1997年起,南汇政府直接投入合作基金,开始在区内实行大病统筹,最高报销可以达到2万元,保障水平提高到25%左右。情况虽有所好转,但并未有根本改观。
多年愿望成真
陆国荣事后知道,就在他内心呼唤政府承担起推进合作医疗责任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构想已经逐步浮出水面。
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表著名的《阿拉木图宣言》,强调了政府对保障人民健康负有责任。我国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明确表示对《阿拉木图宣言》“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目标的承诺。1994年9月至10月间,我国邻邦印度遭受了一场致命的瘟疫,重创了经济和社会发展,仅用于治疗和预防鼠疫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亿美元。这也给中国农村公共卫生安全敲响了警钟。而由于农村合作医疗的瓦解和基层卫生组织的衰落,我国农村公共卫生、预防保健工作明显削弱,一些已被控制和消灭的传染病、地方病死灰复燃,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呼声也日益强烈。
更关键的是对维护广大农民健康、保证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责任,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呼之欲出。2002年10月,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第一次,国务院就农村卫生问题召开专门会议。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加大投入,在合作医疗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当年非典发生后,从中央到各地都加快了“新农合”的推进步伐。
陆国荣回忆,当时,南汇确定了依托洋山港和浦东国际机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目标。而如何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也成了区政府的头等大事。2005年春区人代会上,“加快发展南汇合作医疗事业”被列为一号议案。那时老陆已经担任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当然是责无旁贷,以最饱满的热情投入了新方案的起草。从3月到6月的一百多天里,调研、协调、研讨,夙兴夜寐,反复斟酌,终于,新方案在修改了18遍后得以通过———
从当年起,区镇政府对合作医疗基金的投入,从原来每个农民30元一下子增加到130元,以南汇近40万的农业人口计算,就是一年3000多万元的大手笔。报销封顶的金额提高到5万元,对特别贫困人员,最高报销可达到10万元。多年来徘徊不前的保障率,由此一下子提高到了50%。
百姓拍手叫好,2005年底的参保率猛涨到95%以上。此后政府的投入逐年增加,2007年为每个农民170元,2008年为190元,“加上个人出资140元,和村财务、企业提留等,南汇今年的筹资水平达到了450元。对于南汇这个农业大区,可以说是"跨越式"发展了。我多年的愿望成了现实。”
期盼城乡一体
“明年政府的投入涨到每个农民220元后,南汇农民的保障水平可达到60%。”采访过程中,老陆多次提到60%———这个水平基本可以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需求,也许将长期稳定。而他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尽力和同事们合作,提高管理水平,“让农民参保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医疗上。”
诺言有足够的底气,办法是“以支定收”,即以当年发生的医疗总费用,按照明年计划的保障水平,计算出明年的筹资规模。由于调研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准确,南汇区的新农合资金使用效率很高,一般当年筹集的资金98%都用在了给农民报销上,很少结余。“而且,我们这些管理员的所有开支都由财政出,不像过去要从管理基金中提办公经费。”
老陆特别强调“精细化管理”。10月20日,记者与老陆和他手下的管理员同行,体验了一番如何为农民的钱把关:一整天,几个人埋头在厚厚的资料里,对处方,查病史,检查是否有作假、多报。果然“捉”出了一个“漏洞”,有个村医将本该一次开的珍菊降压片分成了两次开,使得减免的诊察费(从合作基金)多支出了2.5元。虽然村医未必是有意,但老陆还是拉下脸来严厉警告:“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啊,这个头可开不得。”还有一次,老陆从区内的合作医疗网络实时监测系统发现,今年一季度祝桥镇的一些村卫生室支出比上年增加了100%,一调查,原来是开药没有控制好,远远超过了基本药物目录的规定,于是立即纠正,通报全区。
虽然查起账来像“包公”,但老陆和村卫生室的村医们几乎个个都是好朋友。“40多年来,合作医疗都是这些赤脚医生撑起来的啊。”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大家的“苦日子”,如今的村医们都觉得好多了,“有了职称,有了固定工资,退休后还有镇保,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不过,陆国荣也有期盼,现在的村医大多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无论是精力还是水平,已经跟不上现代农民对健康的高要求了。“希望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尤其是提高村医的待遇,这样才能像当年"赤脚医生"那样,吸引本乡本土最有本事的人来做村医,为农民的健康守好门!”
老陆说,上海去年底合作医疗的人均筹资水平达到了450元,发展程度在全国省区市中是最高的,但他仍期望能尽早实现全市范围内统筹新农合的资金,“农民的医疗费用会进一步减轻。”而他的最大梦想,却是不再让合作医疗前面加上“农村”这个限定语———城乡一体化,农民和居民享受同样的待遇、同样的保障。“党的十七大已经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目标,我的梦一定能在不遥远的未来能够实现。这样,我的人生就完美了。”这位为合作医疗贡献了大半生的农家子弟无限向往。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