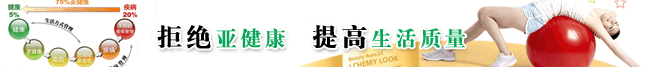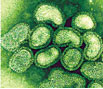5·12大地震距今已经两年半,但造成的破坏与伤害,至今令人不堪回首。在戕害巨量的生命和财产之后,大地震也给存活者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根据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付春胜的介绍,在重灾区北川地区,90%以上都丧失了亲人,大约有24%的人群有心理问题。其中,“孩子这一块达到30%多。老师最初达到40%左右,干部群体这一块达到20%左右。如果对他们不实行专业的干预,他们很难从创伤抑郁中走出来。”外来的救援者也会被灾难所感染,他们的自罪倾向“明显高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心理援助者们大多都把自己和被援助者的相识比喻为“缘分”,但专业的心理援助者,会有意识地针对灾民们的特殊时期和特殊群体进行寻觅。一方面,灾区的被援助对象会经历不同的心理创伤期,而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援助规划、方法和手段,而像泥石流、怀孕失败的经历会令受灾者经受新的打击。另一方面,对于像学生、干部、高龄丧子家长等特殊群体,更需要更特别的关注和谨慎的援助。
专业工作者面临的工作纷繁复杂。在援助的早期,他们需要进行群体性的调查、援助,寻找重点援助的目标对象;随着时间的流逝,二次伤害的出现,以及援助失败个案的增加,幸存者们多样的人生经历、灾难遭遇和人格,就演变成援助者面前的困境。
多位参与5·12大地震救援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在地震发生接近两年半之时,向南都周刊记者讲述了他们所见证的各种心理创伤,还有援助过程中的各种困惑。
更多时间,更多耐心
我原来是精神科医生。其实,灾后精神病人很少,但每个人都会承受心灵创伤。如果精神病医生到灾区是看病的,他看看这里面没有病人,说这里没有精神病啊,不需要吃药啊,就可以回去了。但我们是心理医生,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生活没有信心,譬如,有的灾民本来是做生意,现在地震三个月过去了,还天天躺在床上,眼神还有忧郁。
——史占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危机干预中心副主任
我是跟着红十字会的队伍进入北川县政府的,他们有个部门来接待我。那部门的领导后来自杀了。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因为我跟他仅仅是握了手,擦肩而过,却没有跟他聊聊,帮助化解他心头上的压力。
他们这个部门下面有个女干事,她5岁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了,特别痛苦。我还记得,白天她还问我能不能帮忙,傍晚当我们去找她,她却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我已经烦死了,你们这样子说话的人让我更难受了。”后来我才知道,有些志愿者跟她说,“你只死了一个,有的人死了好几个呢。”
我们国内的心理干预方法,大多是从国外学来的,心理的东西,我花了二十几年去学,但是近几年,我却领悟到很多方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做心理干预,第一步是要接纳对象的全部,第二步是建立信任,让他感受到你对他会有所帮助。另外,很多人会关注幸存者讲述的故事情节,却不关注他们的心情。如果有些问题他不愿意说,就不应该具体问,因为每一遍的回忆都会给他带来痛苦,他会拒绝继续与你沟通。
——沃建中,红十字会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
有一个老太太,地震中老公没有了,死了两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她被人救出来,在北川中学待了一天,直到现在,她还不相信地震这个事,还在到处找儿子,但一谈起她儿子孙子,她就会眼泪哗哗的。她心里还存着希望,而每天希望都会落空,有时她也会意识到家里人死了,因为聊天的时候她会哭,但一直压抑着情绪。这对她心理伤害非常大。
失眠、抑郁、焦虑、健忘、逃避、闪回……这些负面的心理状态她都有。树叶一动,她会一哆嗦,说地震了,就啪啪啪跳开,不跟你细谈;她脑子里还会出现地震的片断。面对这样的高危人群,我们只能两三天去看她一次,让她接受这个现实。
长时间的交往、交流,建立信任关系很重要。志愿者应该至少半年才轮换,如果来七天八天的,我不接受。做哀伤处理的心理支援,必须是半年,因为只有在建立了信任之后,他才会把痛苦说给你听。新来的志愿者,老百姓会说,我要做饭了,没时间跟你聊。他不接受你的帮助。
——付春胜,中科院心理所绵阳北川心理援助工作站副站长
- 2008.06.02
- 2008.05.20
- 2008.06.06
- 2008.05.29